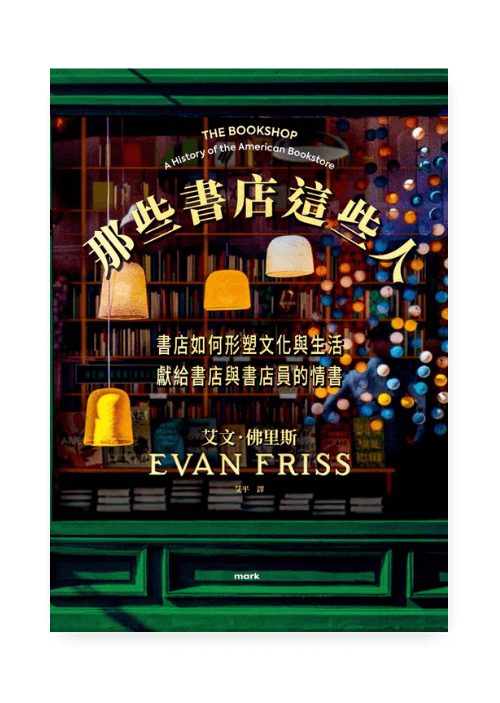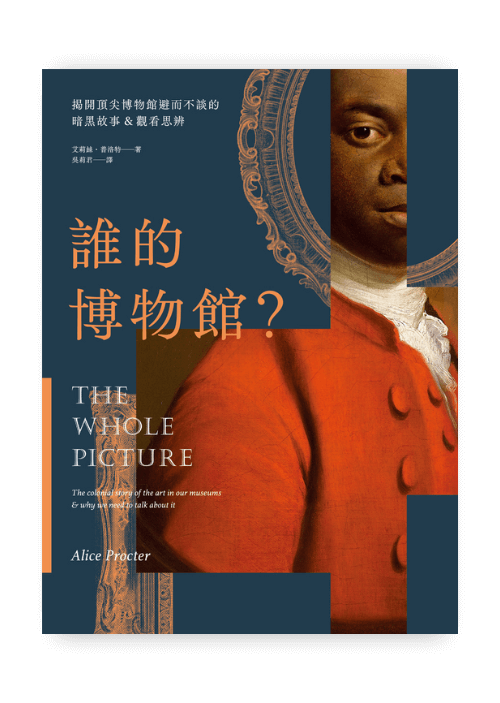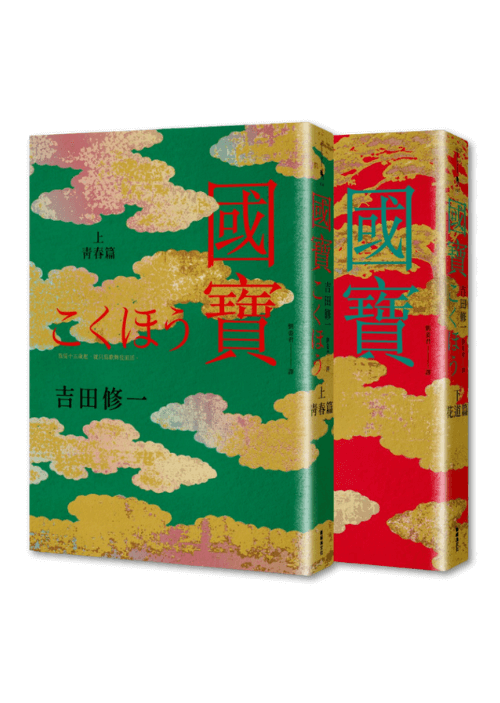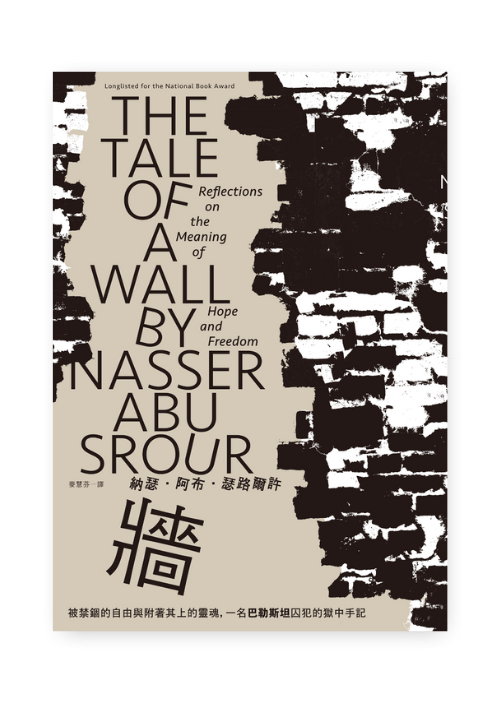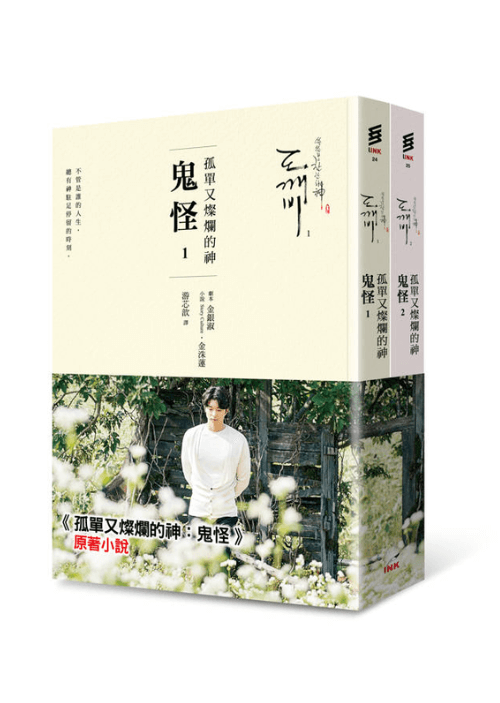可惜,這本書並沒有教大家製作共產主義meme,二次降臨的亦非耶穌基督。
2016年,AlphaGo爆冷大勝頂級人類棋士,美國白宮發佈《準備迎接人工智能的未來》。
2016年,曾被殖民的伊斯蘭世界內戰頻生,其宗教自殺式復仇軍團定期在歐洲城市發動恐襲;西方白人對經濟衰退、全球內戰的恐懼,道成肉身為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總統、精神痛苦蔓延、無差別殺人屢現。
技術與自動化普及的年代將至,結果是指日可待的「歷史的終結」 :資訊過載令人失智,自動化的非人性與普世政治失能、人類復仇之心結合,納粹式機械化滅絕的效率更上一層樓。
二次降臨的,是技術強化版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對此,活躍於社會運動、媒體與資訊科技思想範疇六十載的著名意大利左翼哲學家Bifo(Franco Berardi)重提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的願景:克服國家、宗教和種族分歧,以「被剝削工人」的政治認同,聯合西方工人階級與飽受殖民歷史磨難的數十億人。
Bifo在末世前夕召喚共產主義的meme式二次降臨:以易於複製和記憶的符號、詞語、圖像、姿勢,在後末日再度登場;一切無關意識形態,只為引導技術和自動化走向解放社會時間與締造平等之途。
| 目錄 |
如何
第一章:回顧
第二章:末日
第三章:末日之後還有生命嗎?
| 內容節錄 |
如何 HOW TO
如何面對混沌
對抗混沌的人將被擊敗,因為混沌以戰爭為食。
混沌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它不是客觀的現實:它是人類心智與事件速度之間的關係,那些事件與我們的物理和心理存續相關。
如果有感自己處於混沌的環境,就意味着我們的心智無法以情感處理、以理性決定那些不斷加速、不斷刺激神經的事件。
混沌與意識主體有何關係?啟蒙哲學認為,意識主體理應能將混沌化為理性秩序。但是今天,所有管理混沌的企圖幾乎注定失敗,因為訊息一神經刺激(info-nervous stimulation)早已超出意識能處理的極限。
混沌是以智力化約能力(capacity of intellectual reduction)衡量世界複雜程度的單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混沌是在心理領域衡量訊息領域過度密集程度的單位。
戰爭滋養混沌,以戰爭克服混沌的嘗試都將注定失敗:打擊恐怖主義最終鞏固恐怖主義,維護安全的活動只會增加不安感,打擊假新聞的法律戰爭只帶來炎上風暴。
那麼,在混沌中該做些甚麼呢?來看看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lx Guattari)對此問題的看法:「要對抗混沌,就必須更趨近你的敵人。」
當混沌侵入心靈並吞噬社會行為時,我們不應該害怕它,也不應該試圖將混沌壓制成任何秩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混沌比秩序更強大。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與混沌交朋友。唯有在旋風之中,才能找到新節奏的線索。
無為。
詮釋,而非行動
也許,馬克思(Karl Max)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 )的第十一條論題——過去一個半世紀革命方法論的核心支柱——需要被顛覆。馬克思寫道:「哲學家們迄今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世界;而關鍵在於改變它。」過去一個世紀的哲學家管試遵行,結果卻帶來災難。
哲學家的任務不是改變世界——世界沒有哲學家也會自行變化。哲學家的任務是詮釋世界,也就是捕捉其趨勢,最重要的是闡明其中蘊含的可行性。
這是哲學家的首要任務:解讀可行性。政治家的目光無法看到可行性(possible),反被可能性(probable)吸引。而可能性並非可行性的朋友:可能性是一種完形(gestalt),只讓我們看到已知的,阻礙我們看到未知卻近在眼前的。
詮釋,給予我們解開困結的線索,給予我們逃離迷宮的能力。這個困結就是資本主義,而我的線索是:提升一般智性,必要勞動時間應該隨之減少。如何將這種趨勢轉化為實質地減少勞動時間?這是我的迷宮,為了逃離這個迷宮,詮釋是必須的。
在〈機器殘稿〉(The Fragment on Machines)中,馬克思強調的不是行動,而是詮釋。他希望揭露、轉譯銘刻於「當下」的隱秘之物——即可行性。他檢視知識、技術和勞動時間之間的關係,讀取其趨勢。我們必須使這種趨勢顯現出來——藉着詮釋的力量。
遮蔽
本書是對2017年的哲學描述,當時混沌、痛苦和虛假蔓延全球。
新自由主義幻象破滅為沉迷身份政治鋪平了復歸的道路,但這個幻象的影響力,在金融獨裁的死守之下,雖死猶生。
即使大多數人已經意識到金融獨裁持續撼動西方民主並將許多人推向貧困和絕望,金融並沒有放鬆其掌控。
侵略、殘暴、種族主義和戰爭,是此僵局的結果。
遮蔽情感是此等社會箱制的效應之一。愚昧正在全球蔓延,這是一種反抗,反抗金融掠奪的數學理性:理性遭遮蔽,因為復仇毋須聽從理性。
歷史之終結,眾人曾期待它是歷史理性(絕對理性〔absolute Vernunft〕)的實現;如今,它以金融代碼的數學形態呈現。
數位化捕捉經驗和語言的抽象暴力似乎無處可避。如此,摧毀現代理性再次看似是唯一出路,而我們(從過去的經驗)得知,最終只會事與願違。一般理性羞辱並癱瘓個體,個體因而求助於歸屬感、身份認同和種族的特殊性質。如此,最黑暗的長夜來臨了。
根據薩特惠(Crispin Sartwell) 的觀點:
我們現在痛苦地意識到,我們高估了智慧,以為它是改變世界的力量;是愚昧在左右大局⋯⋯歷史哲學的傳統最高點是確定整體人類的目標、終點或目的地。我推測,特朗普——金正恩辯證是最後階段,在此,歷史同時實現和毀滅自己,也毀滅了我們。
理性不再主宰我們的命運,這點非常明確。
意志似乎也不再是事件進程的主宰,即便晚期現代的權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經常自詡如此。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宣稱,政治權力(君王)建立在暴力地征服現實易變的陰性面向(其拉丁名為機運〔fortuna〕),現代歷史不過是針對陰性特質的永恆雄性戰爭。在現代投向未來的拋物線盡頭,機運(「偶然」〔hazard〕)過於豐富、複雜和不可預測,君王則變得無能為力。技術語言的自動機制取代了理性統治,而無補於事的憤怒和好於侵略的復仇取代了權力意志。
對女性的戰爭,在性、宗教和經濟領域中肆虐。
理性和意志的無能宣告了歷史/他的故事(his-tory)的黃昏,並轉向她的故事(her-story)。
「她的故事」不應被理解為對過去暴力的補償,也不是對女性在「他的故事」(那個迷戀權力、以剝削和壓迫女性作支撐的父權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之肯認,而是以另一種方式,理解我們與時間展開的關係:耗散而非累積,循環而非線性,生成他者而非同一,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節約而非無限增長。
「她的故事」暗示着,相對於自然和無意識不可馴服的力量,應重新調整(亦即縮小)人類意志。「她的故事」意味着,人類意志的全能感是一種相對的假設,也鬆綁了與自由意志幻覺相關的罪惡感。最後,「她的故事」代表着要重新思考人類行為在進化中的重要性。
我們必須從頭開始重新思考主體與進化之間的關係,並隨之重新評估自覺行動和政治工程的重要性。
在歷史框架中,自覺而主動的行動標誌着主體與進化之間的關係。但以我的理解,我們已不再留住於歷史框架之中。
道家思想提出非行動(無為)是進化的唯一合理方式。不是另一個行動,而是非行動。
這是我從2016年至2017年的種種事件中得出的教訓,歷史之光在那時熄滅了。
——摘自本書 P.1- P.9
| 作者簡介 |
貝拉迪 Bifo(Franco ‘Bifo’ Berardi),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媒體理論家與自治主義運動先驅,1960年代及1970年代意大利自治運動的核心人物,創辦A/traverso雜誌與Radio Alice海盜電台;1980年代與法國精神分析師瓜塔里緊密合作。其著作聚焦於精神病理學、資訊科技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互動,探討當代人類困境。
二次降臨:共產主義作為後末世時代的新MEME
作者 | AUTHOR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譚以諾
編輯︰謝莉娜
美術設計︰蘇麗平、許維倫(mmmmor studio)
出版社 | PUBLISHER
手民出版社
書號 | ISBN
9789887072348
出版日期 | PUBLICATION DATE
2025/08
出貨地 | PLACE OF DEPARTURE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