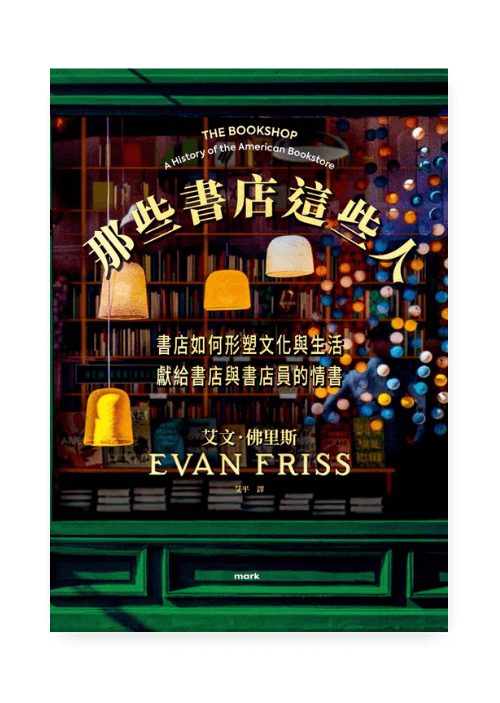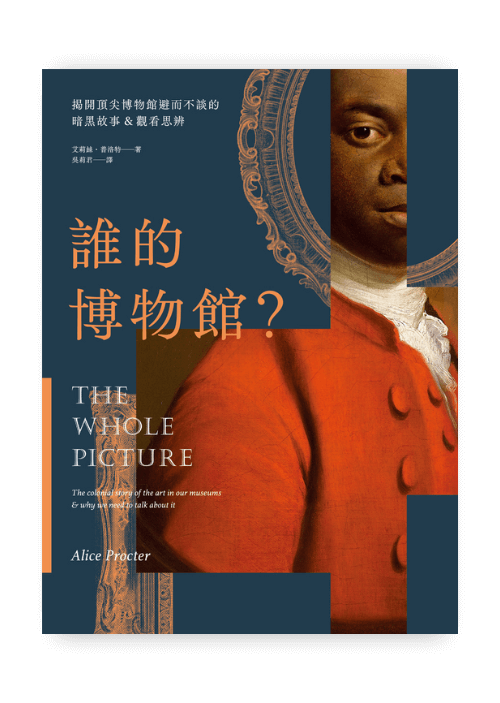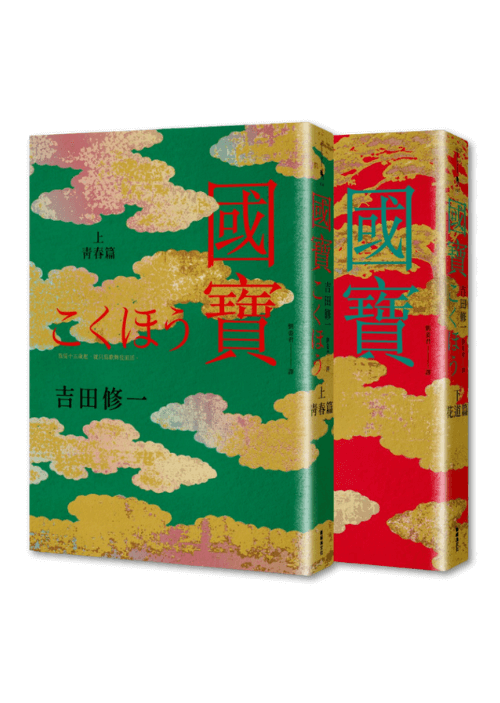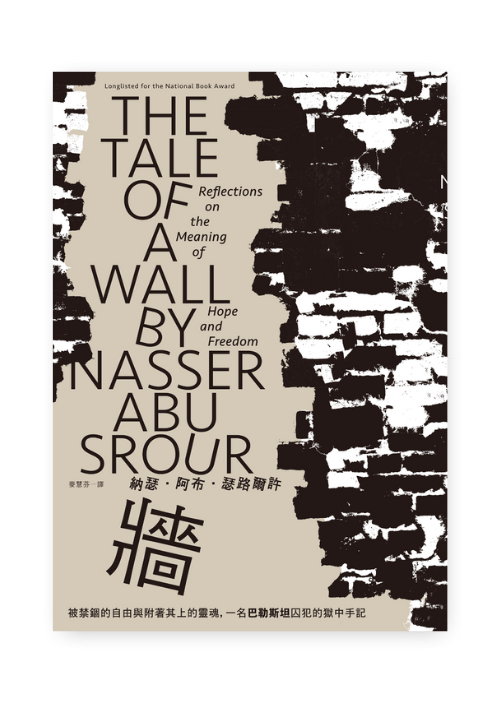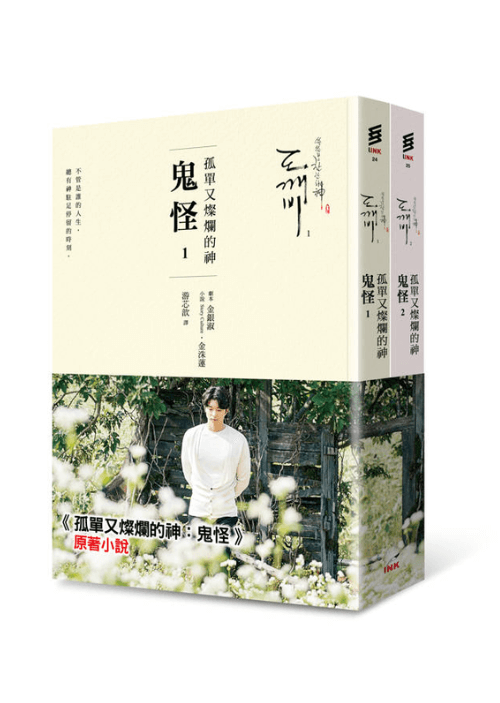「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為何我們會恐懼陌生人,排斥外來者?
◎榮獲美國安斯菲爾德–沃爾夫圖書獎,表彰其提倡多元、反種族主義之價值
◎榮獲伊莉莎白•揚•布魯爾獎,表彰以心理分析拓展對各種歧視偏見之理解
◎彭博新聞社2021年度好書入選
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反猶、恐同、伊斯蘭恐懼等歧視傾向都有個共通點,就是一種稱之為仇外情結(Xenophobia)的心理。排斥與自己不同者,或對外來陌生事物感到恐懼。此種心態與行為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21世紀後越發嚴重,隨著全球化、金融危機、中東和北非難民湧入歐洲,以及中美洲移民向美國前進,西方領導人承受巨大壓力。社會上也出現針對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等少數族群的極端仇恨言論。川普兩度當選總統、英國脫歐、新冠肺炎期間的排斥亞洲人現象,都可說是上述現象之回應。有人用經濟角度來解釋這些仇外行為:資源遭到瓜分、利益受到剝奪,所以才會排斥外來者。但本書作者告訴我們,仇外的理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與政治、社會、心理密切交織的結果。
*舊概念新詞彙:仇外情結的誕生
「仇外情結」自古有之,但這個詞彙真正浮上台面卻在19世紀末。當時遠在東方的中國發生了義和團事件,於是歐洲人將精神醫學界發明的「恐外症」(仇外情結)拿來解釋中國人的行為。他們譴責這種心態,卻沒想過是因自身的殖民侵略才造成此一後果。等到愈來愈多「外來者」從殖民地移入歐洲本土,「仇外情結」才轉為歐洲人對外來移民的排斥,甚至成為一種流行用語。「仇外情結」也與種族隔離、歧視相結合,19世紀的人認為這有利於族群存續,也是人之本性,沒想到卻替20世紀兩次大戰的殺戮埋下伏筆。
*人為何會產生仇外的心理
本書不僅爬梳仇外情結的歷史,也進一步討論仇外情結的產生過程,以及與歐洲百年來思潮的關係。「仇外情結」可能起自19世紀媒體報導遙遠異國的負面形象或是原始社會的野蠻,繼而在眾人心中植入了「刻板印象」,並透過不斷渲染而與「恐懼」情緒綑綁。「仇外情結」也可能是一種內心防禦機制的啟動,將負面情緒「投射」在「他者」身上,用以擺脫內心的衝突。歐洲理性主義認為人是「獨我」的存在,這與後來興起的民族主義,只關注我族、排斥他族同步發展。而本書將透過康拉德、佛洛伊德、沙特、波娃、法農等人的作品與思想,探討此一心理的演變。
*捲土重來的仇外情結
今日,全球面臨極右派勢力興起,仇外情結再次回歸,但並非是21世紀,或在2016年才突然出現,其實20世紀末就已悄悄開始。當冷戰結束後,過去仰賴共同敵人凝聚「民心」的美國或俄國都面臨了內部群體的矛盾衝突,而製造他者並加以排斥成為失去共同敵人後的出路。於是,今日世界的排斥難民、反歐盟、反全球化、甚至階級對立問題,都可以從仇外情結找到源頭。
本書作者為信仰希臘東正教的阿拉伯裔美國人,除了長期面臨認同問題外,13歲時父母的故鄉黎巴嫩開始長達數十年的內戰,原本寬容、多元的國家,一夕間鄰居變成了陌生人,陌生人變成了敵人,社會被恐懼和仇恨所淹沒而解體,加上2016年英國脫歐、川普當選讓他決定去探究「仇外」這個古老的問題。他期望人類能夠破除這種仇外心態,因為人類演化史告訴我們的,克制排外的攻擊行為有利於合作,並建立複雜安全的社會。學會面對陌生人其實不只是維護自己安全的問題,其實也是促進個人與社會可以發展、整合、進步的關鍵。這樣的思考的轉變也是仇外情結的解方。
| 目錄 |
國際好評
推薦序 台灣仇外嗎?台灣好客嗎?/ 杜坤峰(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約聘助理教授)
前言 逃離貝魯特
第一部 仇外心理的根源
第一章 尋找陌生人
第二章 仇外前史:黑色傳奇
第三章 最早的恐懼症患者
第四章 義和團運動
第五章 殖民地恐慌
第六章 揭穿殖民謊言
第七章 移民的迴力鏢
第八章 通往種族滅絕之路
第二部 透視仇外心理
第九章 小艾伯特與恐懼的代價
第十章 刻板印象的濫觴
第十一章 心理投射與扭曲的愛
第十二章 他者之謎
第十三章 自我疏離
第三部 陌生人的回歸
第十四章 我們為何憎恨他們
第十五章 新的仇外心理
尾聲 庇里牛斯山麓
致謝
圖片來源
注釋
索引
| 內容節錄 |
前言
逃離貝魯特
這聽來或許有些荒謬,但我長久以來竟未察覺,這個故事與我的人生有如此深的牽連。我不認為自己已經被完全同化,但或許我已經不知不覺地被同化了。我從未開口說過「我是移民的孩子」。就連現在寫下這句話,我也感到十分彆扭。這句話透露出強烈的被認同需求,卻又顯得虛假,因為我已經很少這樣看待自己了。當被問及「你是外國人的孩子嗎?」時,我總是在承認後,不假思索地列舉出一大串家鄉的優點,試圖證明自己的歸屬感。就像許多移民父母一樣,我的父母也曾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愛國情操常常讓我感到尷尬。然而,即使他們已經成為美國公民許多年,他們一直都明白,那些光鮮的名校學位和獎狀都可能像咒語被破除般,瞬間化為烏有,變成無情的嘲笑,即使是來自哈佛的學歷,也可能因一句口音而黯然失色。
二○一六年五月下旬,我前往倫敦時,完全沒想到這些事。我來這裡只是為了宣傳新書。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英國即將舉行脫歐公投。我對這事一無所知,甚至連奈傑爾.法拉奇1這個名號都沒聽過。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一家羊毛衫店裡,聽到店員興致勃勃地談論著保護英國免遭土耳其人即將大舉壓境的威脅。這讓我感到十分詫異。不過,我當時更擔心的是與文學經紀人即將到來的會面,她肯定會問我下一個寫作計畫。我最近剛跑完馬拉松,身心俱疲,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靈感都沒有。見面後,莎拉這位熱情洋溢的助理,已經準備好了筆記,急切地問我。我支支吾吾,含糊地提到了一個關於「他者心靈」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如何誤解彼此的想法。甚至還提到了賽博格(cyborgs,又稱「生化人」或「半機器人」),真是太尷尬了。我回到紐約後不久,英國就舉行了脫歐公投。幾個月後,美國也選出了新總統唐納.川普。突然間,一個詞語在眾人心中揮之不去。這個聽起來可怕又有點令人困惑的詞彙,許多人同時開始探究它的含義,熱門到一個線上詞典將它評選為「年度詞彙」。1它聽起來有點像「他者心靈」那樣,帶有一點精神病學的意味。作為一名精神病學家,我決定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這個故事的開端,我以為會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自從我們的元祖從非洲東部平原出現以來,人類就一直在遷徙。智人(Homo sapiens)作為一個遷徙物種,會在一個地方定居,然後由於恐懼、敵人、乾旱、饑荒、瘟疫或對地平線另一頭未知世界的強烈憧憬,而繼續遷徙。雖然我們渴望家園,渴望一個被記憶和意義所環繞的安居之地,但總有一股力量驅使著我們不斷往前進。從亞當和夏娃的被逐,到特洛伊戰敗的戰士,或是遠離其台地故土的失落的霍皮族部落2,我們的神話講述了那些從福佑之地出發,卻不知下一個落腳處在何處之人的故事。一旦遺忘的塵埃被拂去,誰又能說自己不是這段遷徙旅程的後裔呢?無論是上個星期乘著小艇逃離家園,還是幾個世紀前隨著一支皇家軍隊遠征,無論是被鎖鏈束縛還是身披絲綢,我們所有人是否都曾在某個時刻,像個睜大眼睛的外星人一樣,在一個陌生而擁擠的地方定居下來呢?
當這些漂泊者登陸或是翻越重重山丘後,他們最終遇見了更早抵達的先行者。陌生人相遇,那些已經在此定居的人往往占據上風。他們會想,這些外來者是否懷有惡意?他們會不會掠奪我們所擁有的?我們會不會變成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基於這樣的恐懼,眾人不僅築起了高高的城牆,還豎起了無形的隔閡。
這種令人不安的相遇,無疑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因此,當得知我正在撰寫一部關於仇外心理(xenophobia)的歷史時,同事們都感到困惑不已。他們不解,我怎麼可能寫一部看似從亙古就存在的人類恐懼的歷史呢?這簡直是唐吉訶德式的瘋狂,彷彿在波赫士複雜的迷宮中尋找出口,又像是要寫一部關於人類笑聲的通史,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從人類最早的文字紀錄來看,許多文明都將陌生人視為恐懼和猜疑的對象。甚至有人認為,在原始社會,所有陌生人皆為敵人。在許多語言中,「陌生人」和「敵人」往往是同一個字彙。由此可見,仇外心理似乎是人類心靈深處的一種痼疾,根深柢固,難以根除。試圖書寫這樣一部歷史,無異於要將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無數鮮血和破碎的頭骨一一拾起,會是一項永無止境的艱鉅任務。
《仇外》無意記錄歷史上所有因為我們現今稱之為「仇外心理」的行為,而遭受虐待、奴役或屠殺的人。而是試圖挖掘隱藏在「仇外心理」一詞背後的另一段歷史。我開始好奇,究竟是誰率先將這種行為貼上「病態恐懼」的標籤,認為這是種不理性的錯誤行為?這種良知的覺醒是在何時、何地萌芽,並逐漸滋長,最終促使一些人高聲宣揚迫害陌生人是不義的暴行?這些聲音是如何建立起一套道德標準,使得眾人逐漸認同這種行為該受到譴責?以及人是如何提出各種概念來解釋這種危險的態度?
二○一六年,當我搜尋「x-e-n…」時,並沒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資訊可以解答我的疑問。搜索結果只給出了一個定義——對陌生人的恐懼和仇恨。然而,與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或恐同症不同,仇外心理似乎沒有清晰的歷史脈絡。搜尋結果中,僅有寥寥幾筆輕描淡寫的提及,大多與古希臘有關,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有價值的資訊。這種資訊匱乏導致一些人認為,仇外心理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空洞的,不過是毫無根據的指控。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仇外心理」一詞似乎成為了描述各種特定歧視行為的籠統代名詞,用以概括針對種族、宗教、民族、性別、性取向或階級等不同群體的歧視。由於每種歧視都具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成因,將「仇外心理」這個概括性概念納入其中,並無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些歧視現象。
我逐漸意識到,這種輕忽是錯誤的。首先,仇外心理和這些歧視形式之間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當我們談論反猶太主義、伊斯蘭恐懼症或恐同症時,我們明確指出被歧視的群體,但歧視者卻往往被模糊化,身分不明。「仇外心理」一詞則導正了這種失衡,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問題的根源,從而開啟了一條更深入的批判性探究之路。正如從喬西亞.羅伊斯到詹姆斯.鮑德溫橫跨一個世紀間的思想家們所指出的,我們的語言往往不自覺地將問題歸咎於「問題群體」的標籤化特質。如同羅伊斯在一九○八年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我們用「白人威脅」而不是「黑人威脅」或「黃種人威脅」來定義美國的社會衝突,情況會怎樣呢?這是否意味著問題出在白人身上?
本書講述了一系列試圖剖析、定義、探究和解答「仇外心理」這個概念的努力。我們的敘述從一場造詞風潮開始,這個詞語的迅速傳播令人矚目。隨後,這個詞的含義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在一九四五年之後,被賦予了強烈的道德和政治色彩。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仇外心理」一詞最早出現在法語和英語中,與西方社會在民族主義、全球化、種族和移民等議題上的關鍵辯論密切相關。因此,本書將以這些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而非旨在成為一部全球史。我無意暗示這種形式的歧視僅限於歐洲和美洲,更不認為相關的道德和政治回應也是如此。這些歷史就留給其他專家去研究吧!
接下來的章節,我將轉向人在面對這種威脅時,所做出愈來愈急切的努力,以找出並消除其根源。為了因應歷史上一系列慘絕人寰的災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民族主義導致的種族屠殺、比利時在剛果所進行的種族滅絕,以及後來的納粹大屠殺——世人開始共同努力,尋找這種如今被廣泛視為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和仇恨的明確根源。思想家們發展出新的術語和概念,例如「刻板印象」、「投射」、「他者」等等,試圖理解這種對於少數民族、外國人和新移民的病態恐懼。接著,我將基於這些研究成果,提出一個初步的、綜合性的仇外心理模型。
本書結尾則探討了我們所面臨的一種突然湧現的,也更為激烈的全新仇外心理。全球科技和經濟的一體化、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中東和北非難民湧入所造成的歐洲移民危機,以及美國所湧現的中美洲移民潮:所有這些事件都使得西方全球化的倡導者承受了巨大壓力,只能被動因應。社會上出現了針對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猶太人、非洲人、黑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等少數族群而來的極端仇恨言論。隨著川普與其白人民族主義盟友的崛起、英國脫歐,以及匈牙利、波蘭、德國、瑞士、法國、義大利和瑞典等國極右勢力的興起,我們再也無法忽視這個事實:仇外心理這個古老的「部落詛咒」似乎捲土重來。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和歷史學家,我通常習慣隱身於幕後。然而,在撰寫這本書時,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欺騙之嫌。我怎麼能寫一本關於移民、宗教衝突、邊界和衰落帝國的歷史,卻不公開探討這些議題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呢?接下來,讓我以我的名字為例來說明。
我的祖父喬治.雅各.馬卡里,一八七七年出生於黎巴嫩的一個小漁村。當時年僅八歲的他,被迫和一個叔叔還有嬸嬸和堂兄一起登上了一艘遠洋客輪。父母在絕望中,將他送上了遠洋客輪。在愈來愈不寬容、日薄西山的鄂圖曼帝國統治下,作為一個希臘東正教徒,他的前途一片黯淡。經過了無盡的海上顛簸,他終於抵達了艾利斯島3。面對入境官員用他聽不懂的語言提問,他感到一頭霧水。官員隨意地為他改了一個新名字:喬治.雅各,這成了他在這片新大陸上的新身分。他們一行人隨後輾轉前往德州奧斯汀投奔親戚。那段時間,年幼的他,只能靠沿街叫賣糊口;他經常受到當地惡霸們的追逐、嘲笑,甚至欺凌。多年以後,他經常向兒子們講述當年的英勇事蹟,驕傲地說起自己如何機智地對付這些粗魯之徒。幾年後,他的弟弟邁克隨後也抵達美國,並被改名為邁克.「麥卡里」——艾利斯島的發音學在此發揮了作用。兄弟倆共同打拚,在一九○九年創立了「雅各兄弟」商店,專門出售土耳其和波斯地毯。他們在店門口掛起醒目的招牌,全家就住在店鋪樓上。五年後,為了尋找更多貨源,喬治預訂了返回故鄉的第一張船票。
我的祖父命運多舛。這位對美國西部故事情有獨鍾、三十七歲的男人,剛踏上幾乎遺忘的故土,就遭遇了一場世界大戰。鄂圖曼人對基督教少數族群展開了大屠殺,海上航行變得危機四伏,更出乎意料的是,蝗災肆虐宛如聖經中的災難景象。協約國實施了封鎖,基督徒被視為內部敵人,僅存的食物被徵收以供應鄂圖曼士兵。大規模饑荒隨之而來,黎巴嫩山脈周圍,奄奄一息的難民在垃圾堆裡尋找橘子皮和骨頭。孩子們只能啃食野草,苦苦掙扎求生。約二十萬人,相當於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殘暴統治者的暴政下慘遭屠殺,成為當時一樁尚未命名的罪行的受害者。身處這場浩劫之中,祖父毅然決然地選擇留下來幫助家人。他恢復了原來的姓氏,結婚生子,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我的父母出生於同一個濱海小村,在鄂圖曼帝國的陰影下成長。那段過往,猶如揮之不去的惡臭,縈繞不去。根據賽克斯-皮科祕密協定,他們的家園成為了法國的保護地,與英國、義大利和沙俄瓜分了這片土地。黎巴嫩,這個多元宗教的國家,匯聚了遜尼派、德魯茲派、什葉派穆斯林、塞法迪猶太人、亞美尼亞難民,以及包括敘利亞和希臘東儀天主教徒、迦勒底人、東方正教和敘利亞正教徒、墨基特天主教徒和馬龍派基督徒在內的眾多東方基督教教派。當黎巴嫩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宣告獨立時,這個國家已經充斥著各種異教徒。儘管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已經撤離了黎巴嫩,但它們的影響力卻根深柢固。它們為爭奪人心,造成我的家庭分裂,分別支持不同的陣營。我的母親瓦達德.塔梅爾在拿撒勒聖母修女會創辦的女校就讀,法國修女們給她取了一個法文名字——奧黛特。她每天上學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唱法國國歌《馬賽曲》。她的日記、禱告,甚至她的夢想,都用她父母無法理解的語言書寫。一百碼外,另一個世界向我的父親敞開大門。他在英美學校就讀,名字從雅各變成了傑克。他在踏入美國大學貝魯特分校前,就癡迷於祖父講述的德州匪徒故事,並且經常背誦有關布魯克林大橋的詩作,那是他從未見過的建築奇觀。祖父在一九三八年車禍去世後,我的父親對那個遙遠的國度充滿了浪漫的幻想,希望能回到他耳熟能詳的另一個家。一九四五年,作為一名年輕的醫生,他獲得了一項在倫敦研究熱帶疾病的獎學金,隨後又申請到了哈佛大學獎學金,開啟了他在美國的醫學生涯。一九五五年,我的父母完婚後,帶著全家移民美國,告別了那個由多元的少數族群組成的故鄉,出發前往號稱多元包容的美國。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美國所標榜的理念——讀者們要審慎判斷——不過是幻夢一場。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喬治‧馬卡里 George Makari,精神科醫生、歷史學家暨作家,近作有《現代心智的發明》(Soul Machin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Mind)。現為德威特‧華萊士研究所所長,威爾康乃爾醫學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精神病學教授。
馬卡里祖籍黎巴嫩,為信仰東正教的阿拉伯人,幼年隨父母移居美國,經常不確定自己是什麼人。1975年黎巴嫩開始長達十多年的內戰,讓原本包容多元的國度陷入殺伐的煉獄,成為他寫作本書、探究「仇恨與排外」的遠因。
| 譯者簡介 |
劉卉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曾任職於出版社,目前為文字自由工作者,譯有《天真的目擊者》、《聖經天使學》、《耶穌與死海古卷》、《白癡的歷史》、《俄烏戰爭》等書。
仇外:義和團、種族屠殺、英國脫歐、川普當選,仇外情結的歷史 Of Fear and Strangers: A History of Xenophobia
作者 | AUTHOR
喬治‧馬卡里 George Makari
出版社 | PUBLISHER
貓頭鷹
書號 | ISBN
9789862627600
出版日期 | PUBLICATION DATE
2025/01/13
出貨地 | PLACE OF DEPARTURE
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