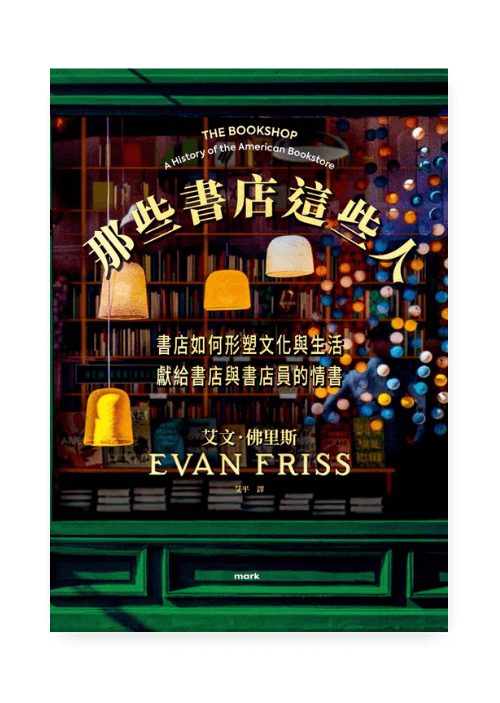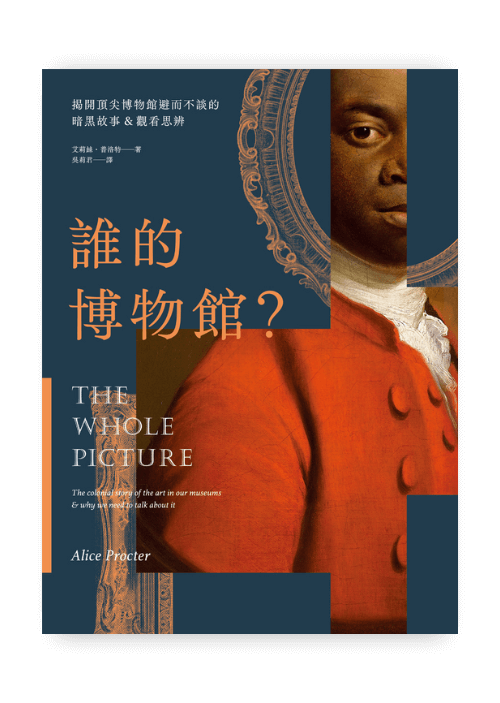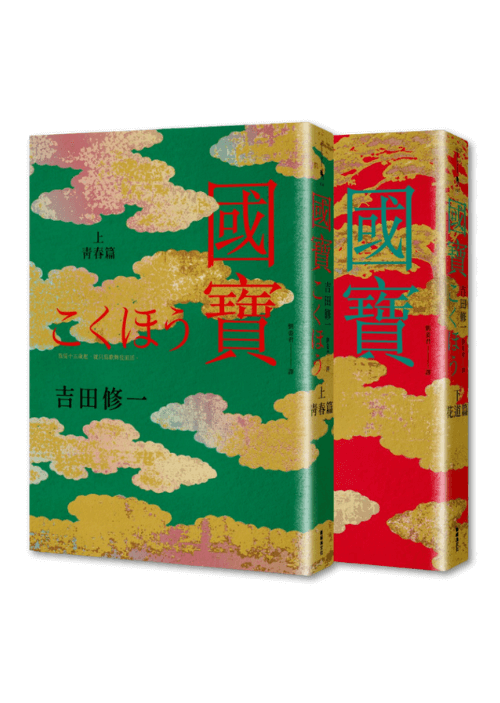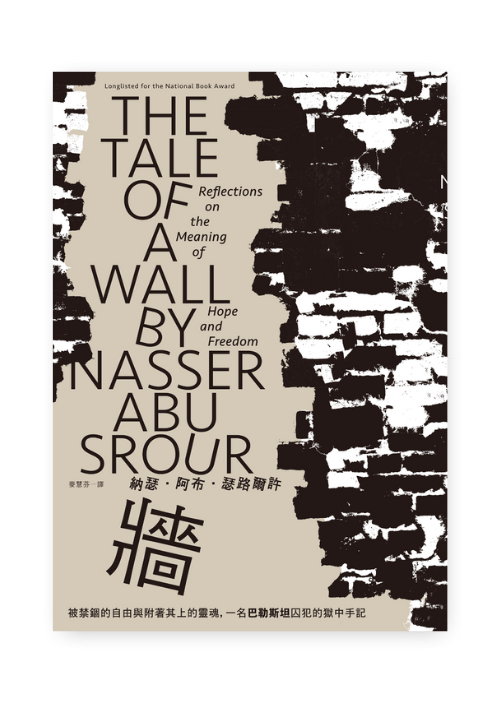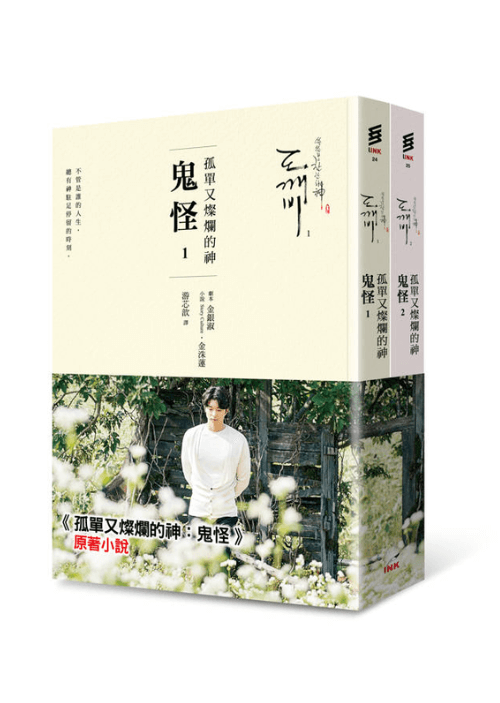弱者的武器:日常抵抗形式的謹慎反抗和精明順從,資本主義滲透下的農民抗爭民族誌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不只有革命才是反抗,從弱者視角重新理解日常中的抗爭
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詹姆斯.斯科特
開創抵抗研究的經典之作
其《支配與抵抗的藝術》《國家的視角》等關鍵著作的核心起點
面對懸殊的高壓霸權,革命必定流血,挑戰招致反噬,難道從屬者只能坐以待斃?
如果只期待轟轟烈烈的革命,必會錯過這些微小卻無處不在的抗爭。
無法公開反抗,那就將抵抗融入日常的點滴之中,
說閒話、假意順從、不合作和拖延偷懶、順手牽羊,或暗中破壞──這些,都是「弱者的武器」。
專業推薦 ▎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宋世祥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林開世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林浩立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鄭紹鈺 哈佛經濟系博士生
「詹姆斯.斯科特學術歷程的轉折點,抵抗研究的開山之作。一本奠基於兩年田野調查的民族誌,細緻地描述了馬來西亞農民在綠色革命的轉型期,如何務實謹慎地對新興的資產階層發動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抗爭。從弱勢者的觀點出發,反對虛假意識的概念以及革命霸權的理論,堅持基本物質生活與生命尊嚴的重要性。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界的經典,推薦給所有懷抱著社會改革理想的人。」──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在馬來西亞農村進行兩年的田野調查後,斯科特以詳實的民族誌書寫,描繪經濟轉型過程中,根植於村莊的社會互惠模式受到資本經濟邏輯的滲透而逐漸式微,亦細緻呈現面對日益嚴峻的生計壓力,農民的具體處境和如何回應經濟霸權者,由此提出另一種觀看政治的視角──「日常抵抗形式」,揭示從屬階級在不公開反抗、組織革命的情況下,透過隱蔽而迂迴的論述和行動,盡可能不損及自身地在壓迫性的結構中進行自我防衛和抵抗。
這是一場扎根於日常生活的持久抗爭,表面的秩序下實則潛藏著無聲的對抗,抵抗那些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力、糧食、稅收、租金及利益的人。農民在公開場合展現「最低限度」的問候和禮物,以忙碌為拖延藉此偽裝罷工……他們運用心照不宣的默契和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採取不易察覺的低姿態,用象徵性的順從換取實質上的不合作,以此對抗難以正面挑戰的體制,同時避開集體反抗所帶來的高風險。
正是數以千計個體的不服從與逃避行為──而非起義、法律訴求或政治壓力,農民經典地展現了從屬者的政治存在感。因此,凡欲公平看待和理解從屬者作為行動者的權力關係研究,都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潛藏於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抵抗形式」。
| 目錄 |
序言
第一章 階級戰爭中的短兵交火
拉薩
哈吉.「掃帚」
權力的象徵性平衡
第二章 常態的剝削,常態的抵抗
未被寫下的抵抗歷史
抵抗作為思想與象徵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和意識
第三章 抵抗的地景
背景:馬來西亞和稻作產業
中層背景:吉打和姆達灌溉計畫
第四章 薩達卡,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
村莊
富與窮
村莊組成
土地使用類型
租賃的變化
稻米生產與工資的變化
在地機構與經濟力量
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階級劃定
在夜裡交錯且互相傳訊的船隻
綠色革命的兩個主觀階級史
雙季稻作與雙重願景
從活租到死租
聯合收穫機
失地:獲取稻田的困難
慈善儀式與社會控制
被記憶的村莊
第六章 誇大事實:意識形態運作中
在特定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工作
剝削的語彙
扭曲事實:階層與收入
合理化剝削
意識形態的衝突:村莊大門
意識形態的衝突:村莊改善計畫
以辯論抗爭
第七章 超越言語的戰爭:謹慎反抗與審慎衡量的順從
公開集體抗爭的障礙
擋下聯合收穫機的嘗試
「常態性」的抵抗
「日常」的壓制
日常服從與掩飾痕跡的抵抗
順從與部分文本
什麼是抵抗?
第八章 霸權與意識:意識形態鬥爭的日常形式
薩達卡的物質基礎與規範化的上層建築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附錄
附錄A: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村莊人口狀況簡述
附錄B: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與一九七九年姆達地區不同土地權屬與農地規模類別的農業收入比較
附錄C:土地權屬變動、淨收益與政治職位相關數據
附錄D:當地術語詞彙表
附錄E:匿名飛信翻譯
參考文獻
照片
地圖
地圖一:姆達灌溉計畫在馬來半島的分布區域圖
地圖二:吉打和姆達計畫區域圖
地圖三:薩達卡村
| 內容節錄 |
序言
一個研究領域的局限性,通常最明顯地體現在其對「何者與該領域相關」的共同定義上。以我自己和其他人所從事的農民研究為例,除了親屬、儀式、耕作和語言等傳統的民族誌主題外,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開始聚焦於叛亂和革命等話題,特別是那些有組織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即便這些運動僅是瞬間的火花,也足以對國家構成實質威脅。我可以列舉出一系列的理由,來說明這樣的關注為何會日漸普及。比如,左派對農民叛亂的高度關注,明顯受到越戰的影響,以及一種如今已漸趨式微的左翼學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浪漫情懷所啟發。此外,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歷史紀錄和檔案,進一步助長了這種浪漫情懷,因為農民只有在其行動對國家造成威脅時才會被提及;除此之外,農民通常只會被當作是徵兵、作物生產和稅收等統計數據的無名貢獻者。至於學者為何會選擇研究涉及農民大規模抗爭運動的議題,其動機不盡相同。有些人著重於探討運動中的外部力量──例如倡議者、激進的知識分子或政黨──在動員那些散漫且缺乏組織的農民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另一些學者則偏好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傳統中較為熟悉的社會運動,也就是那些擁有明確名稱、旗幟、組織結構和正式領導層的運動。對於其他人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分析那些能夠在國家層面推動大規模、結構性變革的社會運動。
我認為這類觀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在絕大部分的歷史中,多數從屬階級很少參與公開、具組織性政治行動的餘裕。更準確地說,這類行動縱使不至於自取滅亡,對他們來說也相當具危險性。即便存在這樣的選項,他們也很難判定是否有其他策略可以達成相同目標。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於改變國家與法律的整體結構不感興趣,反而更關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稱的「使制度對他們的不利程度……降至最低」。正式、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通常被認為是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專利,即使是那些祕密進行或帶有革命性質的行動也不例外。因此,在這個領域中探尋農民政治的存在往往是徒勞的。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地導向了一種結論:在缺乏外部力量的組織與引導下,農民通常難以對政治層面產生顯著的影響。
農民叛亂固然具有重要意義,但它們的出現往往是零星且罕見的──更不用提革命了,其中絕大多數的行動甚至能夠輕而易舉地被鎮壓。更令人感到挫敗的是,即使這些行動極其罕見地取得成功,其結果往往也與農民心中的期望相去甚遠。我並不想否定這些行動的成果,但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就,往往帶來的是更龐大、更具宰制力的國家機器,甚至比過去的政權還要更有效地榨取農民來壯大自己。
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了解農民的日常抵抗形式更為重要。這類鬥爭的形式大多和檯面上的集體抗爭有顯著差異,是農民透過平凡卻持續不懈的手段,對抗那些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力、糧食、稅收、租金及利益的人。在這裡,普通百姓的武器包括拖延、裝糊塗、擅離職守、假意順從、偷竊、裝癡賣傻、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Brechtian)或帥克(Schweikian)的階級鬥爭形式有其共同特徵:它們往往不需要太多的協調或計畫,而是依賴心照不宣的默契與非正式網絡;它們更多是一種個人自助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它們刻意避免與權威發生直接且具象徵意義的對抗。理解這些常見的抗爭形式,能夠幫助我們更加理解農民在歷史中為了捍衛自身利益採取的諸多行動,無論對手是保守勢力還是進步陣營。我猜想,這些日常的抵抗形式終究才是最為重要和有效的手段。正如研究封建主義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指出的:與「農村社區頑強地進行耐心而無聲的鬥爭」相比,那些偉大的千禧年運動只不過是「曇花一現」。這種日常的鬥爭旨在保護農民的盈餘免受掠奪,並捍衛他們對耕地、林地和牧場的使用權。這種觀點同樣適用於研究新大陸的奴隸制度。奈特.特納(Nat Turner)或約翰.布朗(John Brown)那種罕見、英雄式的命定姿態根本不會是奴隸及其主人鬥爭時會出現的場景,我們反而應該更加關注涉及工作、飲食、自主權與儀式的日常抵抗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冒著與當局直接對抗的風險,他們不會為了稅收、種植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而與之對抗。相反的,他們更可能透過不服從、拖延與欺騙讓政策逐漸被削弱。他們寧願漸進式的占有土地,也不願直接侵占土地;他們偏好私自擅離職守,而不是公開發動叛變;他們選擇當小偷,而不會直接去攻擊公有或私人的糧倉。當人們放棄這種策略,而轉向更具唐吉軻德色彩的不切實際(quixotic)行動時,這通常是一種極度絕望的表現。
這種低調的手法與農民階級的社會結構可謂天作之合──農民群體多半四散於鄉間各地、缺乏政治組織,適合此種長期、游擊隊式的防禦性消耗戰。他們個人的拖延與迴避行為被民間流傳已久的抵抗文化強化並且不斷地複製增生,最終將可能使那些首都高層官員所構想的政策窒礙難行。日常抵抗形式或許不會成為頭條新聞,但正如數百萬隻珊瑚蟲任意地結合為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抵制與迴避行為將使他們成為政治與經濟的暗礁。正因如此,農民才得以在政治上發揮其作用。然而,每當政府像船隻一樣擱淺在這些暗礁上時,人們的關注通常集中於船隻本身,而忽視了導致事故的無數微小行為。僅憑這一點,了解這些靜默而無名的農民行動就顯得更為重要。
為了深入研究這一議題,我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期間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待了兩年。我稱為薩達卡(Sedaka)(並非其真實名稱)的這個村莊位於吉打州(Kedah)的主要稻田種植區,是一個共有七十戶居民的小型聚落,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實行雙季稻作。然而,就像許多其他地區的「綠色革命」一樣,雙季稻作使得富人變得更富有,而窮人則保持貧困或變得更加貧困。一九七六年巨型聯合收穫機的引進也許是壓垮貧困農民的致命一擊,因為它消除了小農和無土地農村工人三分之二的工資勞動機會。在這兩年的時間裡,我設法蒐集了大量與此相關的資料。我關注的焦點不僅集中於村莊中實際的抵抗行為,還包含背後的意識形態鬥爭,因為這正是抵抗行動的基礎。在整本書中,我試圖提出對於抵抗、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支配更廣泛議題的討論,以賦予這些議題在實踐和理論上的重要性。
在薩達卡,貧富之間的鬥爭不僅是關於工作、財產權、糧食與金錢的爭奪,同時也是一場關於象徵符號歸屬的戰爭。這場戰爭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詮釋過去與現在的鬥爭,以及辨別原因和評價過失的爭論。此外,這也是一場由不同勢力為當地歷史賦予意義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細節並不光彩,因為它涉及內耗、流言蜚語、人身攻擊、粗鄙綽號、肢體語言與無聲的蔑視。這些事情大多都是在檯面下發生,但在充滿權力的公共場合中,經過精心計算的順從則是普遍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階級衝突需要共享的世界觀。舉例來說,如果沒有共同的標準來判斷什麼是反常、不值得、不禮貌的,那麼流言蜚語和人身攻擊就不會有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爭論的激烈程度取決於其所訴諸的被認為遭到背叛的共享價值觀。爭論的焦點不在於價值觀本身,而在於這些價值觀適用於哪些事實:誰富有、誰貧窮(以及有多富有或多貧窮)、某人是否吝嗇,以及某人是否逃避工作。除了社會輿論的制裁力量之外,這種抵抗形式的許多方面也可以被解讀為窮人對他們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和儀式邊緣化困境的抵制,並堅持在他們所處的聚落中享有基本的文化尊重。這種觀點其實隱含地主張「以意義為中心」來解釋階級關係的價值。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試圖闡述這一觀點對於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宰制與霸權問題的影響。
在薩達卡的十四個月裡,我經歷了一連串的情緒起伏,像是興奮、沮喪、手足無措和單調沉悶,這對任何人類學家來說都不陌生。因為我並不是一名專業的人類學家,所以這段經驗對我來說全是新鮮事。如果沒有F.G.貝利(F. G. Bailey)寄給我有關田野調查的實用講義,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即便有這些明智的指引,我也還是沒有準備好像人類學家那樣,從早上睜開眼睛到入睡之前都必須工作。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大多數待在廁所裡的時候,都只是為了要有片刻的獨處時間。此外,我發現保持緘默且適度的中立態度是必要的,即便這同時也會帶來巨大的心理負擔。隨著我自己的「隱藏文本」(參見第七章)不斷增加,我第一次體會到吉恩.杜維諾德(Jean Duvignaud)的評論有多麼貼切:「在大多數情況下,村莊會向研究者敞開大門,而研究者則是那位時常需要尋覓藏身之處的人。」同時,我也發現鄰居總是對我難免犯的錯誤表示理解,並對我的好奇心有一定程度的寬容。他們容忍了不稱職的我,允許我和他們一同工作。他們擁有既嘲笑我,又與我友好的非凡能力,同時也有尊嚴和勇氣劃出相處的界限。倘若對話熱烈,又剛好不是在收穫季的時節,他們的社交能力足以讓他們聊上一整晚。他們的友善態度表明了他們比我更能夠適應,而我對他們的適應能力則不如他們。我和他們共度的時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意義重大,縱使言語也難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儘管我盡力刪減原稿,本書的篇幅依舊不短。這主要是因為我有必要先把故事講好,才能夠將階級關係的結構和實踐梳理清楚。尤其每個故事都至少有兩面,因此有必要考慮到社會衝突所帶來的「羅生門效應」。此外,納入這些敘事的原因與本書後段的研究目標有關──即從對階級關係的細微觀察,逐步推升到更宏觀的思考。這種更為廣泛的考量,往往需要有這些有血有肉的實例來支持。實例不僅是用以通則化的最佳途徑,它總是比歸納出來的通則還能夠帶出更為複雜且豐富的細節。
除了外來者的正式演講之外,我從未使用過錄音機,都是根據與人交談之際或事後馬上追憶寫下的筆記來進行我的研究。也因此,我所記錄的馬來語有點類似電報的簡略風格,因為只有在對話中較有記憶點的部分才會被記錄下來。我也將翻譯不夠直觀,或是馬來語表達本身很有趣的部分,附加在正文或註腳中。在田野調查初期,我對農村中的吉打方言還不太熟悉,這讓不少村民可能會選擇用簡單的馬來語與我溝通,類似他們在市場上使用的語言。至於特定的吉打方言語彙,可參見附錄D中的詞彙表。
跟大多數農村研究相比,我覺得這本書的出現更像是研究對象影響下的產物。當我開始進行這項研究時,原本的計畫是先完成分析與研究報告撰寫,然後再回到村裡向村民口頭報告我的研究成果,聽取他們的反應、意見和批評。這些村民的回饋將被放在研究的最後一章中,就像是一場「村民的反擊」,或者可以說是由最有資格評論此書的人寫的「書評」。事實上,在我待在薩達卡的最後兩個月裡,我確實向大多數村民蒐集了他們的意見。這些評論通常不僅反映出發言者的社會階級,還提供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批評、修正,以及對我所忽略問題的建議。這些回饋不僅改變了我的分析,也帶來了一個問題:我應該讓讀者先看到我早先較笨拙的分析,然後才揭示村民帶來的洞見嗎?即便最初我有這樣的疑慮,當我開始動筆之後,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假裝不知道已經知道的事情,所以我逐漸將所有的見解融入到我的分析中。這樣做的結果是讓人們低估了薩達卡村民對於分析以及研究素材的貢獻,也讓原本複雜的對話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獨白。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1936-2024)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曾任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同時也是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諳法文、馬來語/印尼語、德文、緬甸語。
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發展、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東南亞、階級關係與無政府主義理論等。其重要著作有《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支配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等,迄今仍影響深遠,成為探討相關領域的必讀之作。
| 譯者簡介 |
賴奕諭,菲律賓研究者。目前就讀於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學系博士班,長期關注菲律賓及東南亞區域的左派政治、原住民族抗爭及政治暴力等議題。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更致力於面向社會大眾的知識推廣工作,包括在轉角國際、故事等議題平台的持續寫作,並積極參與原住民族國際交流事務、文化及人類學科普等相關計畫。
弱者的武器:日常抵抗形式的謹慎反抗和精明順從,資本主義滲透下的農民抗爭民族誌
作者 | AUTHOR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出版社 | PUBLISHER
麥田出版
書號 | ISBN
9786263109599
出版日期 | PUBLICATION DATE
2025/09/27
出貨地 | PLACE OF DEPARTURE
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