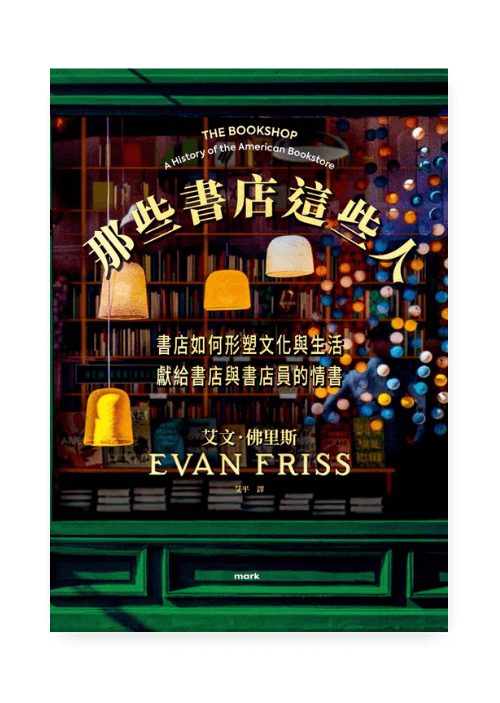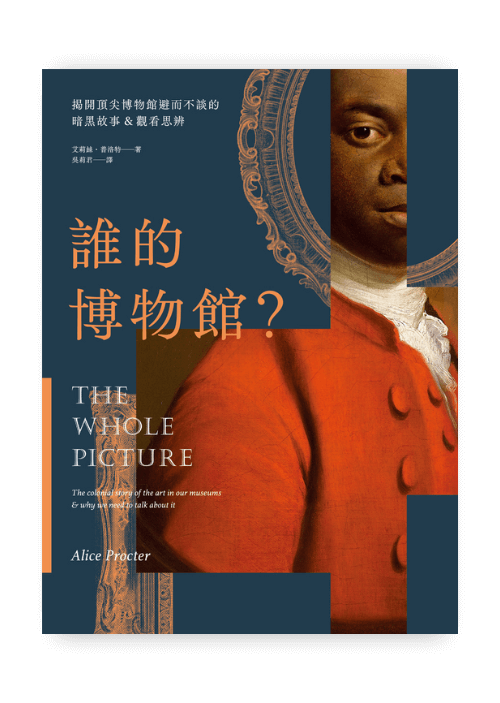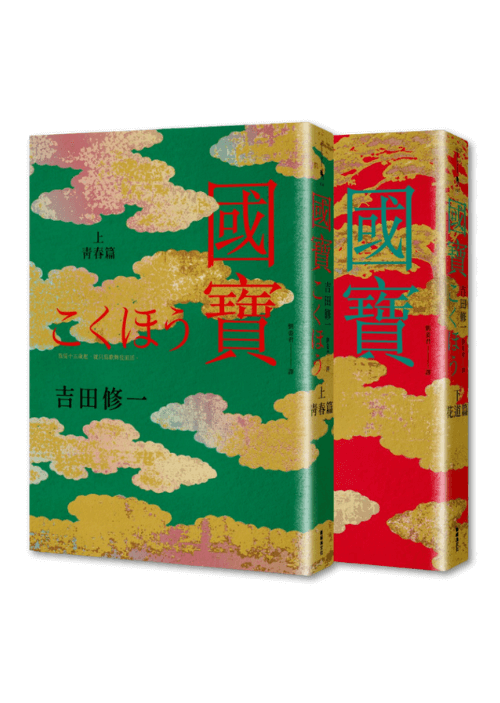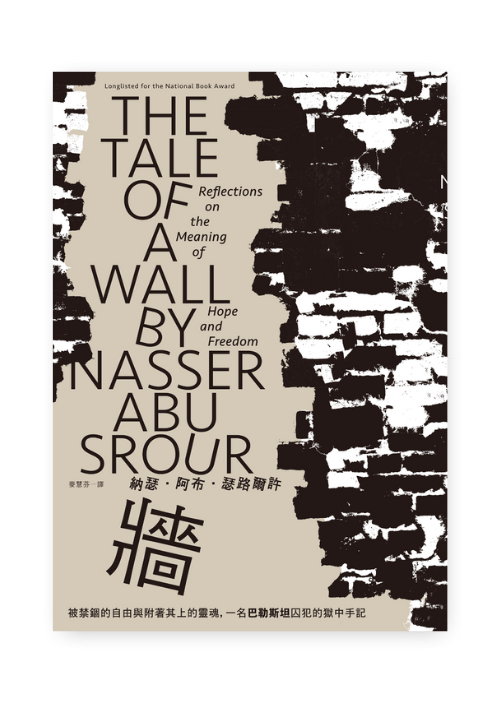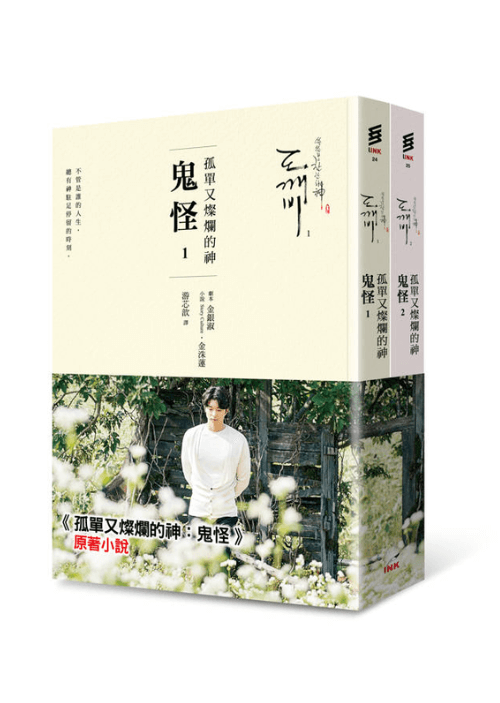徐賁教授繼《暴政史》 及《極權下的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與惡托邦》後,把視角從集中營拉闊至製造集中營的社會:納粹德國和史達林蘇聯。透過剖析在這兩個極權國家裡活過的人的見證敘事,揭示在極權之下過著「正常生活」的人,其內在的心理狀態及面對的外在環境,都是複雜而多變的。讓我們對這段黑暗時期的歷史有更立體和豐富的認識,幫助我們分辨和預防極權的滋生,甚至當極權臨到的時候,個人懂得如何自處。
| 目錄 |
前言 極權下的自我文獻及其解讀
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回憶錄和準自我文獻
1 第三帝國回憶錄的政治因素和人文主題
2 反希特勒回憶錄中的人文主題
3 德國國民性?還是一代德國人的習性?
4 旁觀者社會和「與狼共嗥」
5 怎麼辦和往何處去
6 安身立命與流亡海外
7 準自我文獻的日常生活記錄和評論
8 既是個人又是公共的記憶
第二章 歷史窗口期的史達林時代回憶錄
1 時代夾縫中的回憶和信仰幻滅
2 受命運眷顧的倖存者
3 幻滅與生存:集中營中的喪子之痛
4 記憶是生命的救贖
5 與古拉格受難者一起見證
6 史達林時期回憶錄的雙重歷史背景
第三章 納粹德國日記裏的國民大眾和猶太人
1 納粹時期的不同類型日記和多面形態
2 認識日常生活:日記與回憶錄的互補
3 從日記的自我文獻中發現什麼
4 猶太人日記、政治日記和知識份子日記
5「我要作見證」
6 祕密日記與大屠殺倖存者文學
7 受害者日記的道德反抗
第四章 史達林時代蘇聯日記中的「新蘇維埃人」
1 史達林主義社會中的隱祕日記
2 字裏行間的隱祕時代資訊
3 強制洗腦和「非自由主體」
4 史達林主義下的蘇聯人主體性
5「逆潮流」和「順潮流」的日記
6 日記中的自我改造和政治教育
第五章 納粹體制下日常生活的多重透視
1 研究納粹主義日常生活的不同進路
2 社會史和日常生活史
3 什麼不是社會史或日常生活史
4 納粹主義的象徵與儀式政治秀
5 知識份子的軟弱與妥協
6 納粹的「法治」暴力和恐怖正常化
7 適合日常生活史分析的極權主義主題
第六章 「旁觀者社會」和「自己人社會」
1「旁觀」和「旁觀者社會」的前生今世
2 旁觀者社會和邪惡共謀三階段
3「共識獨裁」和「模糊的中間派」
4 功能性共謀的「裝裝樣子」
5 旁觀者社會和自己人社會
6 史達林主義「自己人社會」中的蘇維埃人
第七章 蘇聯研究中的修正主義與日常生活轉向
1 為什麼不能像譴責納粹主義那樣譴責史達林主義
2 馴服者社會和歸順者社會
3「歷史修正主義」的由來和分化
4 辯解性修正主義:極權主義的恐懼和暴力
5 修正主義的「理解」與「辯解」
6 修正主義的社會史和日常生活史轉向
7 批判性修正主義:對極權主義的曖昧態度
8 極權主義與「社會的人」和「孤獨的人」
9 極權社會及其日常生活
第八章 新聞與學術——史達林時代日常生活的雙重視角
1 外觀視角下的蘇聯生活
2 如何評說蘇聯民眾和蘇聯政權
3 停滯時期的蘇聯社會及其公民抵抗低潮時刻
4 史達林時代的民意難測
5 研究極權主義下「民情」的特殊困難
6 耳語者社會: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私人生活
7 口述史中的蘇聯社會和蘇維埃人
第九章 古拉格和納粹集中營的自我文獻
1 集中營文學:極權主義極端狀況下的自我文獻
2「自我文獻」的跨時代演變及其「雙重性」
3 二十世紀的集中營倖存者寫作
4 兩種極權主義的不同集中營敘事
5 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差異
6 極權體制下的勞動折磨和勞動改造
7 為什麼極權主義的相似比差異更重要
8 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哪個更邪惡?
第十章 旁觀和作惡的社會心理學
1 旁觀者的恐懼與從眾心理
2 道德麻木和作惡的合理化
3 從旁觀者到加害者
4 骯髒的工作和邪惡的人格:蓋世太保和祕密警察
5 殘酷的任務由誰來執行
6 極權主義的殘忍與殘酷
7 個人行為和國家制度的殘忍
第十一章 對納粹主義和史達林罪惡的清算和驅魔
1 對歷史上人道罪行的「清算」
2 關乎清算的「正義」
3 喪失生存價值的「非人」
4 聆聽受害者的聲音
5 假如希特勒像日本天皇那樣被脱罪
6 誰來主持驅魔的儀式
7 命運多舛的「去史達林化」歷程
8 創傷性的過去為何難以消除
9 二十世紀的教訓
結語
| 內容節錄 |
適合日常生活史分析的極權主義主題
日常生活史特別適合分析極權統治下的順從、抵抗和道德模糊等人文主題,因為它聚焦於微觀層面的行為、社會動態和普通人的生活經歷。這種方法使歷史學家能深入探討個人和群體如何在極權主義環境中應對約束,從而揭示傳統自上而下的政治史可能忽略的細節。日常生活史與這些主題契合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日常生活史強調普通人在壓迫體制下的能動性。透過研究他們的行動,歷史學家可以揭示個人如何在求生中進行博弈——從主動順從、投機爬升到消極抵抗或小規模的不服從。例如,透過對個人文獻(如日記、信件和口述歷史)的細緻研究,可以展現人們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無論這些行為在道德上是否正當,還是充滿矛盾。無論是那些參與國家活動(如參加納粹集會)的人,還是那些祕密反對特定政策的人(如悄悄幫助受迫害的猶太人),微觀研究能更好地展示從徹底合作到明顯反抗之間的反應光譜。葛蘭伯格、派恩和弗里奇等學者都透過自我文獻(如日記、書信和回憶錄)來研究極權體制下的日常生活,揭示個人在這種環境中的複雜經歷與選擇。
其次,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常常充滿道德灰色地帶。研究日常決策的細節(如是否舉報鄰居的「反動」行為、是否服從國家命令,或是否選擇對暴行視而不見),有助於揭示人們在外部壓力下的個人倫理與生存需求,也有助於認識他們的道德模糊性。日常生活史揭示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如何重塑社會和道德規範,展示普通人如何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新規則,即使這些行為意味着默許或支持壓迫體制。
第三,日常微觀研究有助揭示個人身上脅迫和自願參與的糾結。像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政權依賴脅迫和自願參與的結合來維持統治。日常生活史探討宣傳、同儕壓力和社會獎勵(如加入納粹組織)如何塑造順從文化,同時研究懲罰的恐懼如何阻止反抗行為。透過關注日常互動的細節(如職場動態、社交儀式、家庭生活),歷史學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極權政權如何滲透私人領域,將表面順從轉變為一種看似正常化或生存所需的行為。
第四,日常生活史研究關注社會關係和信任的扭曲,尤其是極權統治下的社區關係如何被重塑,揭示監控和告密機制如何瓦解信任,製造猜疑的環境。人們往往需要權衡表達不滿或說明別人的風險,面對可能來自朋友、鄰居甚至家人背叛的威脅。例如,納粹德國中的「街區領導」角色——類似街道、城管職能人員——就展示了普通生活如何被深度政治化,幾乎沒有留下純粹道德關係的空間。
第五,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不僅適用於納粹主義,同樣適用於其他極權體制,如史達林主義的蘇聯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它使對不同政權如何使用類似控制機制(如宣傳、監控和獎勵體系),以及普通人如何回應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例如,透過對蘇聯的地下出版,或中國文革期間的地方小報和民間手抄本的研究,可以揭示個人如何在壓迫體系中表達抗議或在道德模糊中生存。這些對比深化了對極構主義作為全球現象的理解。
第六,日當生活史研究揭示了極權統洽下的抵抗及其局限性,這種抵抗往往是零碎的、個別的,是弱者的隨機偶然反抗。透過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個研究方法揭示了在高度控制的社會中,積極抵抗的局限性。它展示了恐懼、疲憊和自我保護的需求如何使人們的反抗僅限於象徵性或私下的行為。同時,這也有助於分析在具體環境條件下,不同弱者的抵抗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納粹德國與史達林蘇聯的日常生活,歷史學家在獲取和利用「自我文獻」(如日記、書信和回憶錄)方面的難度和數量存在顯著差異。相比史達林主義日常生活,納粹主義日常生活的研究更容易獲得這些文獻。這個差異主要源於兩種極權體制在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檔案管理方式上的不同。
首先是文化上的書寫傳統差異。德國人長期以來有保留私人日記、信件和其他書面記錄的文化傳統,尤其是中產階級家庭。這種傳統即使在戰爭和壓迫時期也得以延續。許多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仍然堅持記錄個人生活,儘管存在被監視的風險。在蘇聯,由於對國家監視和告密的恐懼,個人傾向於避免保留私人記錄。自我文獻可能被用作「反蘇」證據,帶來嚴重的懲罰。這種普遍的恐懼情緒大大減少了自我文獻的產生和保存。
其次是檔案可及性的差別。在第三帝國崩潰後,西方盟軍保留了大量關於納粹時期的私人文獻。許多德國移民將自己的個人文檔帶到國外,並捐贈給各類機構。此外,盟軍佔領時期的調查行動也為學術研究收集了大量自我文獻。在蘇聯,檔案的開放度,即使在史達林去世後仍然受到嚴格限制。許多自我文獻被銷毀、隱藏或被國家沒收。儘管蘇聯解體後部分檔案開放,但相較於納粹德國,蘇聯時期個人記錄的可及性依然較低且分佈不均。
再者,流亡者的證詞與文獻也有所不同。許多逃離納粹政權的德國人在流亡過程中寫下回憶錄或保存個人文獻,這些材料後來在民主國家中變得易於獲取,為納粹時代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史達林統治期間,能夠移民的蘇聯公民較少,且多數移民優先考慮生存而非記錄生活經歷。因此,史達林時期流亡者的自我文獻在數量和品質上均遜色於德國移民的記錄。
國家審查制度的影響也是德國和蘇聯不同的原因。儘管審查制度嚴格,但納粹政權有時鼓勵符合意識形態的個人記錄,如青年的日記或愛國活動的記錄。這些文獻儘管帶有意識形態限制,但更容易被保存下來。蘇聯的審查制度更加嚴厲,即使是意識形態正確的文獻,如果政治風向改變,也可能被視為危險品。出於對未來迫害的恐懼,許多人不願將個人思想記錄成文字。儘管面臨上述限制,學者們在研究作品中——如菲茨派翠克的《史達林主義日常生活》及波莉.鐘斯(Polly Jones) 的《神話、記憶、創傷:重新思考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歷史 (1953-1970) 》 (Myth, Memory, Trauma: Rethinking the Stalinist Past in the
Soviet Union, 1953-70)—— 依然利用諸如日記、回憶錄和被國家截獲的私人通信等自我文獻來研究史達林主義的日常生活。這些文獻數量雖少,但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材料和視角。
對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的日常生活史來說,都需要透過將普通人的經歷置於權力結構的背景中,來提供了一種關鍵視角,旨在分析極權主義下順從、抵抗和道德模糊的交織。它捕捉了外部壓力與內心掙扎之間的張力,揭示個人在特殊環境中的博弈手段和反抗方式。透過關注這些切身經歷,這種方法揭示極權主義的人性維度,對於理解控制機制及個人面對的道德困境具有重要意義。
順從、妥協、偽裝、弱者抵抗和道德模糊是納粹和史達林統治下日常生活的重要主題。這反映了普通人在面對極權主義時的複雜反應:有人主動順從以求生存或攀升,有人透過微小的消極抵抗表達不滿,而大多數人陷入了道德灰色地帶,既非完全認同,也未積極反抗。這種道德模糊體現在表面順從中隱藏的內心矛盾,個人的自我保護往往使其默認或忽視政權的暴行。這揚示了在極權社會中,行為與道德判斷之間的張力,以及社會關係如何被扭曲。
這些主題在研究極權主義下的日常生活中尤為重要,因為順從和妥協反映了人們在高壓下的生存策略,展示了極權體制如何透過恐懼和獎懲機制控制行為;偽裝揭示了人們在公開場合和私人生活中的雙重生活,顯示在壓迫下自我保護的複雜性;弱者抵抗強調即使在極權統治下,個人或小群體仍可能透過微小的和日常的抗爭方式表達不滿或維護尊嚴;而道德模糊則揭示了在極權統治下,傳統的道德標準被扭曲或重塑,人性與道德決策變得複雜和不確定。這些主題共同描繪了在極權制度下,個人如何在壓迫與生存之間掙扎,展現了人類在極端條件下的適應性、脆弱性和道德困境。
在研究極權主義下的日常生活時,有另一些相關的主題也常被經常且深入地探討,包括:
監控與隱私:極權國家透過廣泛的監控網路消除隱私,個人生活受到持續的窺視和控制。
宣傳與洗腦:分析如何透過媒體、教育和文化宣傳塑造公眾思想,使其與政權的意識形態一致。
告密文化:研究告密如何成為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導致信任的喪失和人際關係的破裂。
日常生存策略:包括如何在物質匱乏和政治壓迫中尋找资源和機會,適應或規避極權制度的要求。
集體生活與個人命運:探討在集體主義氛圍中,個人如何失去自主性,生活被國家規劃。
恐懼與沉默:研究恐懼如何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導致人們自我審查和保持沉默。
記憶與遺忘:考察極權政權如何操控歷史敘述,壓制歷史記憶以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需要。
性別與家庭:分析極權主義如何影響性別角色、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
文化與藝術:探討在極權統治下,文化和藝術如何被利用或作為抵抗的形式。
這些主題不僅揭示了極權體制對個人生活的全面控制,還展示了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的適應性、反抗形式和道德困境。
——摘自本書 P. 218 - P.223
| 作者簡介 |
徐賁,美國麻塞諸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
極權下的日常生活:見證者的回憶與記錄
作者 | AUTHOR
徐賁
出版社 | PUBLISHER
壹壹陸工作室有限公司
書號 | ISBN
9789887029557
出版日期 | PUBLICATION DATE
2025/09
出貨地 | PLACE OF DEPARTURE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