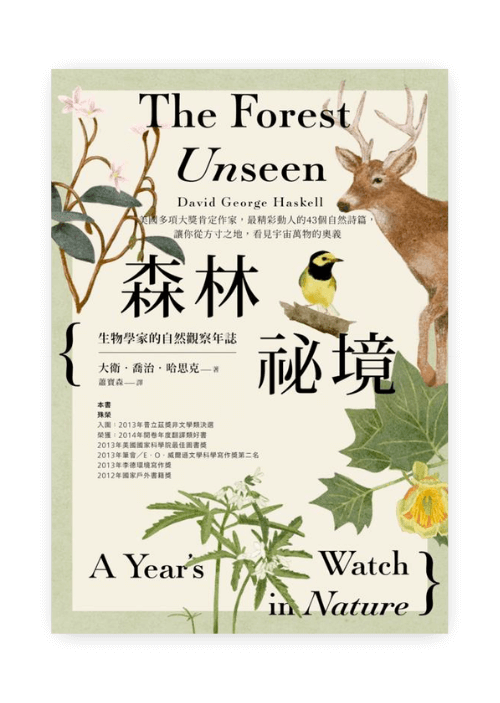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
The Geography of Injustice: East Asia’s Battl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戰爭會結束,但正義不一定會到來
為何二戰後東亞無法如歐洲那般實現和解?
為何戰犯審判未能解決歷史創傷,反而加深了各國間的敵對情緒?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作者最新力作。
◎劍橋東亞系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從散布日、中、臺、港等地檔案重建東亞歷史記憶與裂痕。
◎本書特別收錄臺灣版獨家作者序「臺灣戰後正義的悖論」。
◎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早稻田大學劉傑教授、中研院社會所汪宏倫副所長、輔仁大學蕭道中系主任專文推薦。
中日兩國對二戰一直有著不同的詮釋。相較於德國直面歷史,日本選擇淡化戰爭責任,而中國則以標舉南京大屠殺和攻擊靖國神社予以回應。這背後不僅是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而是東亞的戰爭審判以及戰後處理的方式,給予各國詮釋這段歷史的空間。本書將二戰戰爭審判放入東亞的地緣與歷史脈絡中,帶領讀者了解這段歷史如何形塑且至今依舊影響著東亞各國的局勢。
讓位給政治的戰爭記憶
二戰結束後,全球有50多處法庭展開對日審判,在美國主導且國際法未臻成熟的情況下,留下大片空白與爭議。尤其是東京大審,有人質疑:這是一場為了滿足復仇而動用虛假的法律程序。戰後美國選擇不追究天皇的責任,更在冷戰期間將日本視為地緣政治下的盟友,對戰犯問題採取寬容態度。到了197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他們開始重新定義戰爭罪行,並抗議同盟國在戰後所推行的正義,甚至透過重寫歷史,試圖翻轉國際形象。有些開始將二戰「正名」為「大東亞戰爭」,詮釋成一種解放亞洲之戰,或是將日本對中國與對歐美的戰爭理由分開,後者是為了防禦而戰,並非一種侵略行為。
當法庭不是用來追求正義
戰爭法庭本身既可成就正義,也可能掩蓋不義。當記憶與歷史出現裂縫時,日本社會借用審判重新詮釋自我身份。至於中國,審判的目的也不僅是為了處罰戰敗國。國民黨政府曾透過戰犯法庭進行大規模公開審判,試圖重建戰後秩序與主權象徵;而中國共產黨則傾向以政治改造方式處理戰犯,讓法庭轉化為政治教育的展示場域。兩者雖方式不同,卻都將法庭作為建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舞台。
戰爭記憶形塑的東亞政治
在本書中,作者提出競爭正義的概念,正義是一個漫長、複雜且充滿競爭的歷史與政治過程。在戰後去帝國、去殖民、樹立政權合法性和重塑國族認同等歷史脈絡中,各國領導人都為了政權合法性和重塑國族認同,而利用了戰罪審判與相關歷史記憶。而這些未竟的爭論也都塑造出今日東亞的政治地理。所謂的正義是否施行,記憶是否和解,不僅僅是法庭上的審判可解決之事,而是我們如何去理解與詮釋過往的歷史。如同台灣複雜的歷史記憶,讀者將可透過本書從歷史、法理、地理與政治交織處,探索二戰後的記憶之戰,挖掘形塑今日中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國家之間的關係與東亞局勢之關鍵所在。
| 目錄 |
好評推薦
臺灣版序言 臺灣戰後正義的悖論/顧若鵬
序言 一次失敗的節目製作經驗
第一章 日本敗戰後的東亞萬象
第二章 正義的形貌:創造國際道德水準新象徵
第三章 你眼中的英雄,別人眼中的惡棍
第四章 日本的戰爭責任落在何方
第五章 「小決定、大暴政」:日本左翼的失敗
第六章 日本本土之外的帝國解體暴力
第七章 權力地理:在中華民國創造政治遺產
第八章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創造法律大戲院
第九章 正義病理學:盟軍佔領結束後的日本
第十章 幕後祕辛:戰後中日對正義的態度受到哪些力量影響
第十一章 消失的法律記憶與國民黨戰犯
第十二章 戰爭的解釋權:打造國族歷史的輪廓,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
第十三章 罪人身後事:紀念正義與不義,一九九零年代到現在
結論 東亞政治野心的貧困
致謝
注釋
檔案來源
索引
| 內容節錄 |
序言 一次失敗的節目製作經驗
二○一九年五月底,在一個酷熱的日子裡,我搞砸了。當時的我身處中國北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子,坐在一個矮得不可思議的沙發上,而我要做的只是在鏡頭前向我的訪問對象提出一個簡單問題。那絕對是我這輩子做過最糟的一次訪問。
「你問他,」電視導演這樣說。她催促著我,「問他他妹妹發生什麼事了。」這位導演也身兼翻譯,負責在我聽不懂方言時幫忙。她斜坐在我右邊,鏡頭拍不到的地方,一直催我開口;但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心裡知道完了。我明白,就在這一刻,這場訪問已經以一種意料之外的方式脫離我的掌控。天氣太熱,汗水浸濕我的襯衫,流淌著從我臉上滴落;屋內通風很差,空氣黏膩。我應該要在鏡頭前主導整場訪問,但實際上卻是接近荒腔走板。
前一年冬天,中國上海的主要電視臺之一與我聯絡,問我有沒有興趣主持一部關於二戰後中國舉行戰罪審判的紀錄片影集。討論這個主題的書籍不多,其中有一本就是我的著作,而且影集腳本的某些部分是用我那本書當作模板;既然如此,那我應該順理成章地答應邀約。但我卻有所猶豫,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媒體報導的公開性與可信度方面的紀錄並不怎麼好看。簡單說,「第四權」在中國並沒有發揮作用。新聞檢查極其嚴格,沒有任何機構組織或媒介被賦予「向當權者呈現真相」的任務。然而,同時我也覺得,如果能去中國,與這個團隊(由充滿熱情的年輕中國記者組成的高水準團隊,我的擔憂也是他們努力面對的困境)共事,我能見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是怎樣書寫歷史、怎樣設想歷史。簡而言之,身為一個研究日本的專家,我可以利用這機會踏遍中國各地,拜訪那些一般情況下我接觸不到的地點與人物。我可以看看地方上的中國人怎樣看待中國與日本的歷史關係,並親身感受這些新聞怎樣成形、怎樣報導。
於是,此時此刻我在這裡,荒野中一個塵土飛揚、灰濛濛的小村,表現失常。試問,你要怎樣有技巧地向一名九十出頭的老者詢問他的親人是怎麼死的?這位中國老農的家人死在戰時日本皇軍的某場攻擊行動中,而我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試圖追問當時私密的過程細節,卻總得不到想要的回答。當他向我們揭述那一件定義他人生的恐怖往事,我如果還在鏡頭前做出微笑、傾身向前表示我在專注傾聽,這模樣未免也太過虛偽。
我試著開口,但我突然發覺自己做不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難以用字彙組成一個問題。情緒淹沒了我,這一刻太令人招架不住。我多年來都在研讀日本皇軍士兵所留下的供述,讀他們在中國犯下的恐怖暴行,也讀中國人對這些事件的回憶。我埋首於戰罪審判的文字紀錄中,閱讀日軍的戰場報告與日記,裡面是這些人承認身犯何罪。我原以為自己已經百毒不侵,結果卻發現,比起書面文字,從親身經歷者口中直接聽到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體驗。原來我不管在心理上或甚至是學術上,其實都非常缺乏準備。所以,那時候,我就坐著,一語不發。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見證這些事。我相信,當一個人面對衝擊他的理解或令他說不出話的時刻,他應該做的就是坐下來聽,「傾聽」,也就是仔細聽對方說什麼,並提供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給予同情並小心拿捏分寸的方式。
攝影團隊與我來到河北省的北疃村,訪問幾名在年輕時經歷過一九四二年慘案的農人。那年五月底,日本皇軍的一個陸軍大隊對這座村莊進行掃蕩,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勢力。村莊下面有密密麻麻、縱橫交錯的黝暗地道,當時還年輕的李慶祥為了躲避日軍而逃進其中一條。日本在一九三八年加劇對華侵略,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和當地人開始挖鑿地道。這些人缺乏武器,但有強烈的抵抗決心,他們在軍事力量與戰爭謀略上遠遠不敵日本皇軍,只好在地底挖隧道來自衛。地道戰成為中共反抗軍的金字招牌,後來有好幾部賣座的中國電影都以這類戰役為題,甚至還翻拍。為了把地底下這股反抗勢力驅趕出來,日軍往隧道裡投擲毒氣罐,留在地道裡的人(大多是婦女和兒童)因此窒息死亡,而逃到地面上的通常在地道口就被圍捕,有些當場被日軍處決。地道裡暗無天日,不僅恐怖,且令人難以呼吸;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確定方向——我現在是在往北邊、往村外走,還是在往東走向另一處戰場?只有當這人大著膽子從隱藏的地道口探頭出來,他才有可能獲得安全。李慶祥帶著一個妹妹一起逃命,但迷宮般的地道裡一片混亂,他們倆都大口喘著粗氣時,而他沒有抓牢他妹妹的手。當他終於回到地面上,妹妹已經不在身旁。是我們要求李慶祥接受訪問,但當他開口說起這場悲劇,我馬上就後悔了。「我跟著我母親,還抱著一個小妹妹……我手裡的妹妹,她八歲了,她說哥哥,我走不了了,你們走吧。實在是太黑了看不見,你說我怎麼顧得著她?所以說,你們問我這個我不願意說啊,我要說了,我這好幾天吃不了東西。」他回憶起當時,眼中溢滿淚水。「我心裡難受,我要掉淚啊。我妹妹說,哥哥你走吧,我走不了了。我一出去,〔他哽咽住,無法說完整句話〕她就死在那(地道裡)了。」
屋內突然被寂靜籠罩。我應該要問下一個問題,但當坐在我旁邊椅子上的那個人正從心底深處掏出那段屬於他個人的可怕回憶,我應該怎樣繼續訪問下去?我很慌張,為了這段他被我們要求而回憶起,發生在我出生之前的另一個時代的悲劇,我想伸手去握他的手,給他一點安慰。我什麼都不能做,但我卻是應該掌控全局的那個人。我不知要如何反應,因為無話可說。整個氣氛讓人非常難受,一分一秒流逝的時間像是永恆那麼長。幸好,導演在此時介入,讓我沒把情況弄得更加狼狽。但問題在於,這場面不是製作電視節目的好材料。導演之前跟我解釋過,電視節目裡必須有事情在進行,必須有行動、有活動(這點在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的電視節目裡都一樣)。如果我們在這時候去拍李慶祥的臉,可以拍出很有震撼力的畫面,拍到他被逼著記起他試圖遺忘的那件事時眼中的淚光;但這種做法實在太廉價。最後,我只能說,那是個讓人非常不好過的一天。
很不幸的,儘管發生在李慶祥身上的悲劇如此使人揪心,質疑的聲音卻依舊存在。不論是日本犯下的戰罪,或是替戰後東亞裁決正義的戰犯審判,這些歷史都有很多爭議。事實與虛構的差異,或事實與「能在法庭上被證明的事實」之間的差異,導致我們直到今天仍有空間可以去詮釋當年那座中國小村莊裡,或說亞洲這整場戰爭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距離戰爭結束已經超過了七十五年,但各方對於「正義是否真正得到伸張」的問題仍有歧見,這加劇了東亞地區的政治衝突。日方的詮釋質疑北疃村大屠殺、李慶祥浩劫餘生的故事,而這些質疑至少有日軍官兵最早的供述內容作為根據。國民黨從來不曾向日本追究這場慘案。直到一九五六年,也就是北疃村慘案十四年後,中國共產黨才將此案告上他們自己設立的特別法庭,並讓參與其事的日本軍官招認罪行。然而,不幸的是,特別法庭審判成果才過幾個月就從大陸的媒體上消失,隱沒在其後數十年他們內部打擊「反革命」的鬥爭之中,同時其裁決也遭其他各國漠視。這種集體失憶的情況是怎樣出現的?原因又是什麼?我在本書中都會加以解釋。日軍戰罪的很多中國受害者要等到一九九○年代,更確實地說是等到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才得以討回公道。
若要理解今日東亞政治區劃,「東亞戰罪審判留給後世的影響」是一個尚未獲得充分探索的切入點。原因在於,這些審判以各種互相競爭的東亞現代史敘事將戰爭與帝國綁在一起。日本當然該為自己做過的事負全責,但有不少個別的人在戰後未受追捕、沒被送上法庭,也有不少人的受難血淚直到數十年後才被紀念,這其中原因值得探究。與普遍的認知相反,戰後東亞之所以未能實現正義,並不只是因為日本人不想道歉而已。以戰罪審判為源頭,各方對於日本這個帝國的定位與意義展開辯論,引出各種分歧的政治與歷史觀點,這才是整個不諧狀況的起因。也正因此,本書中「正義」一詞並沒有一個單一定義——簡單說,就是單一定義並不存在。日本與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都以各種天南地北的意識形態為由,要求實現一種烏托邦式的正義,但這種目標卻不可能透過法令達成。我敢說,這是因為「正義」在這裡是透過較長期的協商折衝得到實現,所以會變成跟我們對過去所進行的歷史重現糾纏不清(或是因此而變得無效)。
關於正義的不同設想之間當然存在區別,東亞語言文化專家李海燕就對中國的「高級」與「低級」正義做出更充分的闡述。「高級」正義是與國家利益有關的問題,「低級」正義則是因為個別人民受到不公待遇而懲罰加害者。但李海燕的研究方向是從主權國家角度檢驗「正義」這個概念,而我這本書是要探究「追究正義」的歷史遺產,在這地區歷史與政治中扮演何種角色。我的假設是:當我們設想如何跨國實現正義,這件事就不可能純粹靠法律達成,而要透過公約與實踐來進行。正義是受害方與加害方都同意而達到的結果。也正因此,不管政治家有多麼想宣布歷史結束、正義昭彰,這都是不可能的;歷史沒有結束的一天,歷史永遠在進行,我們對過去的詮釋也永遠在改變。任何「歷史已經抵達終點站,各方已徹底達成共識」的宣告都注定讓人失望、注定以失敗告終。如果各方要真正和解,必須一直進行互動對話。所以說,「和解」與「正義」是兩種不同的過程。在一國國內,正義可以是結論,可以有一個最終聲明,可以在法庭上當庭宣布(但我們不應把這個跟國際歷史解釋混為一談)。出了國界,國際和解沒有終點,其基礎是各方當下與未來的行為。歷史從未停止,我們無法真正讓討論或爭議終結。
為了追蹤各國國內與國際關於正義的對話之路,我在書中會讓日本與中國的相關章節輪流出現,讓那些不是東亞專家,也不曾深入了解其中任一個國家的讀者,能將戰罪審判歷史視為「區域性司法時刻」來檢驗。前面幾章追溯二次大戰結尾這段歷史,同時回顧中國與日本的帝國競爭源起。接下來幾章探討那些形成東亞戰後探求正義之旅的憲政法域和法律行動,以及中日兩國自身怎樣投入這些(經常是彼此對立的)的過程。後面幾章將研究範圍擴大到戰罪審判結束之後,檢驗判決結果如何演變成一種很粗糙的工具,既被用來影響外交政策,也被用來製造出各種「記憶工業」,而更進一步刺激當代東亞社會輿論。
第一章 日本戰敗後的東亞萬象
二次大戰之所以在亞洲爆發,起因是當時日軍在中國北平1城外暫駐的軍營中有一名年輕士兵失蹤。這人可能只是內急跑去解決,也可能是迷路迷了一陣子,端看每個人相信哪種說法。日軍駐軍地點與中國北方的國軍(國民黨軍隊)非常靠近,情勢高度緊張,而接下來的一系列措置失當與誤解又讓事態急遽惡化。這名失蹤士兵過不久就回營報到,但這個「情事變更」並未上報給指揮體系;這件事,再加上當晚零星響起的槍聲,對日方來說足以構成開戰理由。日軍聲稱中方即將發動攻擊,因此他們必須反擊。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部隊是「關東軍」,他們急切想要強化滿洲國這個傀儡國家,並在日本占領區與南邊的中國軍隊之間製造出緩衝地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清晨,日軍以密集火力攻擊小鎮宛平。宛平鎮雖不起眼,卻擋在盧溝橋這個橫跨寬闊河床通往北平的交通樞紐前面。這場短暫交火引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未宣之戰(中國政府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底才正式宣布進入對日作戰狀態)。鄭福來今年九十多歲,但當年日軍在盧溝橋與國軍激烈交戰之時,他還只是個小男孩。今日的宛平仍是小鎮,但裡頭熙熙攘攘,到處都是遊客,接待整車整車前來的中國學童,以及其他為了獲得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手資料而到處跑,把宛平當成其中一站的訪客。
鄭福來是個很難訪問的對象,因為他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多少年來他都在講同一套話給中國小學生聽。也因此,不管我們問他什麼,都很難讓他脫離固有的回應模式。他說,他在盧溝橋附近,河的另一邊長大,他還記得日軍發動攻擊那一天,記得之後日軍在該地區大幅增兵。但他記得更清楚的則是一九四九年解放軍進入宛平,他津津樂道地重述當時情況。中國共產黨宣布「人民當家作主」,鄭福來鏗鏘有力地說,「他們要求士兵不准偷民眾糧食、不准擾民。」鄭福來暗示說,解放軍不會從當地人那裡拿東西,這種紀律讓附近村鎮居民都印象深刻;他還興高采烈地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因為相比之下國軍做這種事一點都不手軟。
距盧溝橋不遠處就是戰爭博物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這是一座龐大建築物,裡面有無數標語提醒訪客「勿忘國恥」,牆面處處掛著這四個大字,像是鄭福來那套單向獨白的視覺呈現,逼人把它刻在腦子裡。當我詢問鄭福來關於那段歷史的問題,他從來不會暫停一下開始回想,或是先思考怎樣回應。他給出的回答已經不是他個人的,而是背誦出來的記憶,且他每講幾分鐘就會插入一段話來讚頌共產黨拯救現代中國。他很少去說戰時實際發生什麼事,也很少說到國民黨(抗日戰爭戰鬥主力)所扮演的角色。聽完鄭福來的話、看完抗日戰爭紀念館,我們會以為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反感是源自二次大戰;這麼說也沒錯,但事實上「勿忘國恥」的教訓還有更深層的含義。中日衝突早在盧溝橋事變將近五十年前就已開始。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顧若鵬 Barak Kushner,歷史學家,目前擔任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教授,2025年獲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主要研究範圍是日本近代史,包括日本文化史、中日關係史。1990年畢業於布蘭戴斯大學,2002年再從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除英語之外,精通漢語、日語和法語。妻子是知名日本外交官水鳥真美。
著有《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遠足文化,2021。
| 譯者簡介 |
張毅瑄,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臺灣大學化學系畢業。譯有《黎明的守望人》、《人類預測大歷史》、《哺乳動物們》、《地球毀滅記》、《古典洋裝全圖解》等書。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若以求知的觀點看待一切,所有的事都是好事」。
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
作者 | AUTHOR
顧若鵬 Barak Kushner
出版社 | PUBLISHER
貓頭鷹
書號 | ISBN
9789862627785
出版日期 | PUBLICATION DATE
2025/08/09
出貨地 | PLACE OF DEPARTURE
台灣